其他国外企业社会责任界说述评
编辑:中国验厂网 来源:作者:郑汉根 动态来源:现代法学 日期: 2008-03-29 17:19:09
导读:
企业社会责任是20世纪初以来凸现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等国诸多学科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亦是建构企业与社会和谐关系的一种基本思想。作为理论概念,企业社会责任蕴涵隽永,言近指远,然于其诠释,歧异颇多,即便是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者中,也未能就其形成一致公认的学说。作为极富建设性的思想,企业社会责任风靡不衰,众多理论工作者殚精竭虑,意在唤起人们对它的认同与接纳,然又因其挑战传统而备受责难。鉴此,当我们思考在我国应否树立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时候,有必要首先追问: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于企业社会责任,我们应作何把握?本文是站在倡导企业社会责任的立场上着手讨论的。其主旨,在于通过对国外具有代表性的企业社会责任界说进行回顾和检讨,发掘企业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义,进而寻求企业社会责任在我国的恰当表达方式。一、国外学者观念中的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观念发端于美国,探究企业社会责任的本意,自应从美国说起。形成于20世纪初美国学界的企业社会责任思想,尽管最初几无系统而直接的归纳,然其大致旨趣依然是较为明了的。在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早期开创者那里,企业社会责任是对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目标之外所负义务之概括或表达。申言之,传统企业及企业法理论以最大化企业利润、进而最大化股东利润为企业的惟一目标,主张企业法律制度的构造应紧紧围绕此一目标而展开。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者则认为,利润最大化仅仅是企业目标之一种,除此之外,企业尚应以维护和提升社会公益为其目标;企业法律制度须在企业的利润目标和公益目标两个维度之间维持衡平。在这二元的企业目标中,前者集中体现的是企业及其管理者对股东的义务,后者着重反映的则是企业及其管理者对企业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义务。因非股东利益相关者具有相对广泛的社会性,“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作为表示企业及其管理者对其所负义务的一个简约说法,便由是得以确立。对“企业社会责任”一语的歧义主要产生于日后围绕企业社会责任所开展的争论之中。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反对者中,大多数人从根本上拒绝“企业社会责任”一说。他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提法有悖企业的本质和企业法的传统,且其含义不可识别,故而无法获致认同,更不能成为法律上可操作的概念。这种认识在早期的“贝利-多德论战”①中即已初见端倪,而后又被一些传统理论的信奉者明确化。Gunness就曾经总结道,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大部分批评,缘自它隐含着这样一种信念:对于众多困扰社会的问题之解决,企业负有直接的责任,并且它们有能力单方面解决此等问题——这至多不过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奢望。[i] Smith也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一词含义模糊;单凭此点它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他看来,“企业社会责任”“只不过是一种宣传工具而已。这一语词从未对企业的行为标准作出过描述,仅仅是充当企业、管理者及消费者团体之间相互斗争的武器罢了。”[ii]形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上述思想,也对大陆法系国家的一些学者产生了深深的影响。例如,韩国商法学者李哲松教授即鲜明地表示,对将“企业社会责任”或“企业社会义务”视为法律上的概念,乃至将其引入公司法的看法,他不能苟同。因为,其一,“企业社会责任”一说有违企业的本质。在他看来,企业乃纯粹的营利性团体,企业保有此一传统的、固有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能起到作为企业手段的应有作用;若公司法引入企业社会责任,则很容易使公司法的架构逐渐变为公益性质,当政治权力迎合一般民众对企业积累财富的反感时,这又必将进而成为制裁企业营利的借口。其二,企业社会责任的义务内容具有模糊性。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一说没有明确赋予任何作为义务,无法起到行为规范的作用;若将其反映于立法中,则有可能成为立法本应极力避免的“空白规定”。其三,企业社会责任的义务对象并不存在。他指出,对于社会责任向谁承担,谁可以作为权利人请求履行之等问题,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迄今皆未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惟笼统地以消费者、一般大众、企业所属的社会全体等来表现之,但这些笼统的集团是不能作为现实的权利人而存在的。私法上并无无权利人的义务,把企业社会责任引进公司法,即必违背此一基本原理。基此,李哲松教授进而结论道,企业社会责任并非法律上的约束;如果被这非法律概念误导,在与董事固有的善管义务相同的水平上考虑它,则只能引起混乱。[iii]李哲松教授的这些认识,可谓最集中、最全面地概括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反对者拒绝“企业社会责任”之说的理由。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反对者中,另有部分人士并不一般地拒绝“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提法,而是在“企业社会责任”名下,装入“利润最大化”之内涵。在他们看来,只要企业竭力追求利润最大化,即等于践行了其对社会的应尽之责,因为包括企业在内的每一经济个体实现利润最大化,必达致全社会福祉的最大化。Drucker是较早提出这一思想的学者。他指出:“牟取利润是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责任是绝对的,是不可放弃的。”并且他还认为,私益和公益可以自动调和,在此意义上,“私益和公益是一致的。”[iv]弗里德曼是持此观点的另一位代表。他一方面对本来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大加挞伐,将其斥为“一种极具颠覆性的学说”,另一方面又指出,在自由社会中,企业负有一项且仅负一项社会责任,这就是在游戏规则许可的限度内,倾其所能,利用其所控制的资源,从事旨在增加利润的各种活动,或者说无欺诈地参与公开而自由的经济竞争。[v]这些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最大化利润目标等同的观点,伴随着自由思想的传播和流行而在理论界获得了广泛的市场。应当说,此等以亚当·斯密式的视角对“企业社会责任”一语所作的注解,尽管于形式上保留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外壳,然就其实质而言,则与拒绝“企业社会责任”之说并无二致。与企业社会责任反对者的态度迥然有别,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者对“企业社会责任”一说大都表现出明确的认同。Stone承认“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模糊的字眼”,但他又认为,“正是缘于这种模糊性,才使得该词获得了广泛的支持。”[vi]Votaw也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精妙的词汇。它有所指,然其意涵在不同人的心目中又并非总是一致。许多人仅将其与慈善捐赠等而视之;某些人则以为它意指社会良心;众多这一提法的热烈拥护者则把它视为'正当性’(Legitimacy)的同义语;另有少数人将其看作一种信义义务(Fiduciary Duty)——一种赋予商人的比加予一般民众的行为标准要求更高的义务。”[vii]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者中更有不满于企业社会责任之含义模糊者,面对来自企业社会责任的反对者就企业社会责任语焉不详之状况所作的指责,他们苦心孤诣,力图揭示企业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义,由此形成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各种界说。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所作的种种表述中,除前述那种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企业在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的义务之传统认识外,首先值得展示的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是以外延式的方法(Extensional Approach)对企业社会责任所作的界定。这其中最著名的范例,当数美国经济开发委员会对企业社会责任所作的表达。在1971年6月发表的一篇题为《商事公司的社会责任》的报告中,美国经济开发委员会列举了为数众多的(达58种)旨在促进社会进步的行为,并要求公司付诸实施。这些行为涉及10个方面的领域,它们是:(1)经济增长与效率;(2)教育;(3)用工与培训;(4)公民权与机会均等;(5)城市改建与开发;(6)污染防治;(7)资源保护与再生;(8)文化与艺术;(9)医疗服务;(10)对政府的支持。美国经济开发委员会在罗列了如此范围广泛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后,进而又将其区分为两个基本的类别。其一是纯自愿性的行为,这些行为由企业主动实施并由企业在其实施中发挥主导作用;其二是非自愿性的行为,这些行为则由政府借助激励机制的引导,或者通过法律、法规的强行规定而得以落实。[viii]第二种有必要专门予以介绍的观点,是在“企业责任”(Corporate Responsibility)这一属概念之下,通过对各种企业责任的比较来把握企业社会责任的意含。[ix]它以Brummer的认识为代表。依此种思路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含义的学者认为,企业责任可划分为四种,此即企业经济责任(The Economic Responsibilities of Corporations)、企业法律责任(The Legal Responsibilities of Corporations)、企业道德责任(The Moral Responsibilities of Corporations)和企业社会责任(Th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Corporations)。企业经济责任乃企业传统的和固有的责任,系指企业所负有的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责任。企业法律责任被界定为法律所明定的企业义务。因企业在传统法律上是作为实现私人经济目标之法律实体来对待的,企业经济责任常寓于法律之中,故企业经济责任与企业法律责任于事实上很难区分。但在一些学者的心目中,此二者仍属不同的企业责任类型。他们提出,企业经济责任所表明和强调的,只是这样一种意含,即谋求旨在实现股东经济利益的特定的企业目标毋需法律的特别要求;而企业法律责任所重点揭示的,是企业负有应法律的要求而为牺牲利润行为之义务。作为企业责任组成部分的企业道德责任在既往的理论中并无直接、简明的界说,此方面已有的认识,大都是从探究企业道德责任的构成着手,来把握它的基本意义的。综观各家之说,于企业道德责任之成立和归责条件,学界所及,概有四点:(1)企业对行为的性质和可能的后果具有充分的理解能力;(2)行为对人类福利具有重大影响;(3)企业有能力对行为及其后果加以控制;(4)社会对行为的标准有一定的要求;若当事人的行为低于社会给定的标准,或者在其行为中引起有害性后果,则应受到指责甚至惩罚。在对企业经济责任、企业法律责任和企业道德责任作出上述界定后,这些学者又通过对比的方法,展现企业社会责任在其心目中的基本含义。他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之妥适与否,取决于其能否满足一定的条件,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它是否有“合理边界之存在”(the Presence of Rational Boundaries);此所谓“合理边界之存在”,意指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必须承认和尊重企业的其他类型的责任。基此认知,他们进一步考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他种企业责任的区别。在他们看来,企业经济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之不同,在于前者重点反映和关注的,乃一类范围相对狭窄的人的利益与要求,这些人主要是指与企业有着最直接牵连的股东;而后者侧重体现和强调的,是更为广泛的社会公众的利益和愿望,这里的社会公众,尤指那些受企业行为影响的第三人。企业社会责任并不一定如企业法律责任那样直接规定于法律之中,这被学者们视作是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法律责任的基本区别点。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道德责任的区分,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表达。Strier认为,与企业道德责任不同,企业社会责任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某个集团或社会公众的期望而形成,此等期望可能与社会的道德观点有着惊人的一致,但又并非总是如此。Cooper则力图从两方面对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道德责任作出区分。首先,他认为,与企业道德责任不同,被视为是履行社会责任的行动不必总是属于当事人职责范围内的行动;怠忽社会责任或者未能履行社会责任的不良后果,亦不一定就是不可接受且应加以避免的。基于这种认识,他还对企业因在履行社会责任中作出不完善的或者有危害的决策而应当受到道德上归责的观点提出了猛烈的质疑。为了进一步说明其论点,他给出了这方面的一个例证。他指出,企业责任给企业管理者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其中之一,就是要竭力使企业在市场中得以生存和发展,但鉴于市场的多变性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企业破产的正常性,力求企业的存续与壮大也就成为超越企业管理者职责范围的额外要求,企业管理者尽力使企业在市场上保持营业便是一种社会责任而非道德责任,其在这方面未获成功亦相应地不应受到道德上的指责。其次,Cooper指出,企业道德责任必须是对人类福利有相对重要影响的企业责任,而企业社会责任并不产生这样的影响。在他看来,在企业管理者履行企业责任的各种行为中,遵守企业文化设定的某种限制,包括有关如何着装以及在工作岗位之外怎样行为等方面的规范,即属负担社会责任而非道德责任;若经理人员在某天身着不得体的服装上班,或者,他们在业余时间宁可沉迷于体育运动也不愿为慈善团体或社区组织作些贡献,则他们仅仅忽视了社会责任而不能构成对道德责任的违反,相应地,他们亦不应受到道德上的谴责,因为他们的行为不会对第三人造成什么重大损害。企业是否向非营利性的大众文化教育电视提供资助,也属同样的情况。与上述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济责任、企业法律责任和企业道德责任并列的认识不同,另一种极具代表性的企业社会责任定义则把企业社会责任看作是一个涵盖各种企业责任因之几与企业责任等同的属概念。在持此观点的众多学者中,又以美国佐治亚大学教授Carroll最为著名。Carroll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乃社会寄希望于企业履行之义务;社会不仅要求企业实现其经济上的使命,而且期望其能够遵法度、重伦理、行公益,因此,完整的企业社会责任,乃企业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得自主决定其履行与否的责任(即慈善责任)之和(Tot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 Legal Responsibility + Ethical Responsibility + Discretionary/Philanthropic Responsibility。[x] Carroll进一步解释道,经济责任反映了企业作为营利性经济组织的本质属性;尽管把经济责任作为社会责任对待似乎有悖传统,亦有些奇怪,但事实上本该如此。因为使企业成为营利性的经济组织,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要求,而让企业尽可能营利,又是自由企业制度的应有之义,由此决定,在理解企业社会责任时,即不能像有些企业管理者和学者那样,将企业的经济功能与企业的社会功能对立起来,而应把它们作为相互匹配、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共同纳入企业社会责任的框架之中。Carroll还指出,社会通过准予企业生产、销售产品以赚取利润,从而造就并维持着我们的经济制度,但企业对利润的追求也并非是无所限制的,社会同样要设置一定的规则——法律,企业只能在法律的约束下实现其经济职能。由此,企业法律责任应运而生。企业法律责任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编辑成典的伦理(Codified Ethics),因为它包含着正义这一基本的伦理道德观念。与企业法律责任不同,企业伦理责任是未上升为法律但企业应予履行的义务,它含蓄着广泛的企业行为规范和标准,这些企业行为规范和标准,体现了对消费者、雇员和当地社区心目中的正义价值观的全面关注,也反映了尊重和保护股东权利的道德精神。至于所谓得由企业自主决定其履行与否的责任(或企业的慈善责任),Carroll认为,这是指企业参与非强制性的或者非由法律和伦理所要求的社会活动的义务。其所揭示和表达的,乃社会要求企业成为出色的团体公民(Be a Good Corporate Citizen)之愿望。企业伦理责任与得由企业自主决定其履行与否的责任仅有细微的差别,这种差别在于,后者于道德或伦理意义上的强制性不如前者那样明显。换言之,若一个企业未按某些利益相关者集团之期望为慈善之举,则这些利益相关者不得将该企业归入不道德者之列而加以归责。总之,在Carroll看来,企业负有的上述四种责任尽管含义有别,但都是社会希望企业付诸履行的义务,因之皆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组成部分;惟有力争牟利、遵守法律、重视伦理并乐善好施的企业,方堪称为真正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以上三种企业社会责任界定方式,集中反映出学者们对企业社会责任外延的不同把握。除此之外,于企业社会责任之定义,学界的分歧还体现在其他诸多方面:[xi]其一,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构成是否应以企业管理者具有慈善的或者热心公益的动机为条件,Haas、Loevinger、Manne、Ackerman和Bauer等学者持肯定的态度,他们认为,惟有本着提升公共福利之主观愿望而牺牲经济利益者,才能归入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与此相反,以Davis、Blomstrom、Starling和Sturdivant为代表的学者则主张,在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界定时,其着眼点应放在行为的特定结果或效应上,亦即一定的企业行为能否被视为是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取决于该行为的社会影响和实际效果,无论有无慈善动机,只要它在事实上有益于社会公益,则皆属践行社会责任的行动。其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中应否包括“自愿”的内涵,Manne、Jones和Wallich以为,企业社会责任必须是完全自愿性的,它不是由法律或者外部经济压力强加的。而以Strier、Sethi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则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精髓,就在于它是外在的力量以某种方式加予企业的义务。此等外在力量,通常是指社会的期望,有时亦表现为市场的压力。其三,就“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是否含有为经济上的牺牲之意含而言,以Manne、Haas为代表的学者持鲜明的肯定态度,并且主张,惟有在经济上作出付出之行为,方属企业社会责任行动。而Bock、Davis、Blomstrom等学者则表示,企业践行社会责任与其实现利润最大化之间并不必然地发生冲突。在他们看来,企业社会责任目标与利润目标的最终协调,这是一个尚有讨论余地的问题,而不能如同Manne和Haas那样,断然地把此二项目标的协调视为不可能,故此,不可将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行与企业利润目标的实现对立起来,亦无必要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中注入诸如“经济上的牺牲”之类的内涵。其四,于“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究竟强调的是行为的过程还是行为的圆满完成,学者们的认识存有歧异。一些企业社会责任的评论者指出,企业担负的社会任务缺乏切实落实之保障,企业管理者亦不能最终实现其所宣称的企业社会目标,这已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为突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行效果,有必要把企业社会任务的“圆满完成”(Successful Completion)作为“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的重要属性。与此相反,Starling和Jones等人士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主要表达的应是企业追寻社会目标的过程,企业实施的一项行为是否属于履行社会责任的行动,主要并不取决于其是否实际达到预定的目标,只要行为的过程足以表明企业是在为实现一定的社会目标而努力,即便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亦不得否认其社会责任性质。二、对国外企业社会责任诸界说的评价与取舍由上文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企业社会责任”一语所表达的蕴意在早期国外学者的心目中是较为确定的,但伴随着日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之争,不仅“企业社会责任”一说的妥适性受到了传统理论信奉者的猛烈质疑,而且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者也根据其各自的判断或理论建构的需要,为“企业社会责任”一词注入了各种不同的意含。这迫使我们对不同的观点进行斟酌取舍。限于本文的主题,以下对学界在界定企业社会责任时所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之科学性与正当性问题将不作探究;这里的评判所涉及的,只是企业社会责任倡导者的若干思想。(一)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济责任的界分企业社会责任的本来意义及其最初与企业经济责任之区分,应当说是甚为明确的,它实则创设于企业经济责任之外、独立于企业经济责任并与企业经济责任相对应的一类企业责任。企业经济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这种区分,是早期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据以提出和构建的基点;亦是早期传统理论的信奉者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者之间开展“对话”的出发点——尽管传统理论的信奉者拒绝企业社会责任甚至斥之为异端邪说,但他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者所言“企业社会责任”之意旨,仍然是理解的,尤其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他们所一贯亲信的企业经济责任之不同,亦是意识到的,在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者进行的论战中,他们更是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经济责任的对立面而加以反击的;尽管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极其青睐,但他们对企业经济责任之独立存在仍是认同的,他们无意于以企业社会责任去吸收或取代企业经济责任,更不希望以企业经济责任去包装或改换企业社会责任从而使其披上企业经济责任之外衣,而是试图在企业经济责任之外另行赋予企业以一类新的责任。然在后来,伴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之争的逐步推进,企业经济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众说纷纭,二者的界限也变得愈来愈模糊。除有部分学者坚持此二者的传统区分外,亦有学者以自己的理解或为了特定论证目的之需要,对企业经济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作出有别于传统观念的说明。这其中,又以将企业经济责任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组成部分的认识最为普遍。在上述“企业社会责任”的诸界说中,美国经济开发委员会倾向于区分企业经济责任和企业社会责任。②尽管在其罗列的10类对社会负责任的行为中,第一类即“经济增长与效率”同企业经济责任极为相似,但它重点涉及的,却是具有社会责任性质的对企业在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总体要求。③这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企业经济责任,是并未被美国经济开发委员会纳入企业社会责任范畴之内的。Brummer将“企业经济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平行的概念,一起归在“企业责任”项下,也表明他对此二者是加以区分的。但与这两种认识截然相反,以Carroll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则视企业经济责任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通过将企业经济责任纳入企业社会责任,他们试图建立一种企业对包括股东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但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中,企业社会责任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与企业责任等同的泛概念。将企业经济责任定位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构成部分,可谓近年来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上的一种新观念。持这一观点的学者通常都将自己认识建立在如下推断之上,即,企业利润与社会福利存在着一种正相关关系,即利润最大化,亦意味着社会福利最大化,在企业利润具有此种社会功能之意义上,企业对利润的追求,也是对社会福利的追求,以利润最大化为其基本内涵的经济责任,自应归入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显然,这一对企业经济责任的把握,与亚当·斯密、弗里德曼等自由学派代表的视角极其相似,惟一明显的不同,在于前者除把企业经济责任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看待外,还强调企业负有其他方面的社会责任;后者则倾向于把企业经济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等量齐观,认为企业只有一种可以接受的责任或者说社会责任——经济责任。应当说,这些学者的推导过程并无错误,但我们认为,此种将“企业经济责任”归作“企业社会责任”下位概念的做法,与其说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毋宁是对企业社会责任反对者的妥协,因为它试图在“企业社会责任”之中装入“企业经济责任”的内容,以此博得企业社会责任反对者的同情、支持或接受。其进一步的结果,是改变了企业社会责任应有的和本来的意义,背离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建构的初衷,同时,使“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一种无所不包的“大杂烩”,进而不仅使“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理论构架基本概念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存在疑问,而且模糊甚至掩盖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济责任的冲突,也使解决这种冲突的努力可以轻易被忽略。总之,确立企业社会责任,并廓清企业经济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揭示企业社会责任同企业社会责任的矛盾统一,在此基础上寻求二者的衡平与良性互动,这是早期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者孜孜以求的目标。为了更好地朝着这一目标走下去,我们应当正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济责任的不同、它们之间的冲突。Carroll那种将企业经济责任归入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位法,是失之偏颇的。 (二)关于各种企业责任间的关系如上文所示,在学界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界定的讨论中,除“企业经济责任”外,学者们涉及到的用语还有“企业法律责任”、“企业道德责任”、“企业伦理责任”和“企业的慈善责任”(亦即得由企业自主决定其履行与否的责任)。按照学者们的解释,“企业法律责任”乃规定于法律中的企业义务。这是企业必须予以履行的责任,它反映了一定社会对企业基本责任范围的认知以及对作为正式制度的法律在落实企业基本责任上特殊功效的信仰。与企业法律责任不同,在学者们的语义中,企业道德责任、企业伦理责任和企业的慈善责任都不直接规定在法律中,其落实也主要依靠舆论、风俗、习惯等法律以外的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从严格意义上讲,企业道德责任与企业伦理责任并无二致,国外学界亦总是交替使用二者以表达相同的意义,但在对企业道德责任(或企业伦理责任,下同)的解释上,不同学者们采取的方式又有所差别。如前所述,以Brummer为代表的学者以一种晦涩、玄妙的解释法,力图从多角度确定企业道德责任之边界。依此解释法,一项企业行为要成其为企业道德责任,须同时具备四个条件,即:企业对行为的性质具有充分的理解能力;行为对人类福利有重大影响;企业可以对行为及其后果实施控制;社会对行为的标准有一定要求。这种对企业道德责任的Brummer式的解释,颇为新颖,但很显然,它不能使人们对企业道德责任与企业经济责任的区分获致一个清晰的概念,亦难以对企业道德责任与企业法律责任的差异作出合理的和令人信服的说明,更不能对企业道德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给予恰当的展示。④相对而言,Carroll将企业道德责任界定为未上升为法律但企业应予履行的义务,这种界定较为简明,也符合学界、尤其是法学界对道德责任的通说。但Carroll在确立企业道德责任的同时,又提出了一种新的企业责任——企业的慈善责任。在Carroll看来,与企业道德责任一样,企业的慈善责任也不体现在法律中,二者的区别,惟在后者的约束力稍不如前者,它是纯粹的得由企业自主决定其履行与否的责任。事实上,若以法学的视角来判断,Carroll所谓企业的慈善责任,实际上属于道德责任的范畴;大多数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者也正是把企业的慈善责任作为企业的一种道德责任来对待的。由此看来,从法律的角度审视,英美学者在探讨企业社会责任时所提出的企业责任的下位概念,可以简约化为四个,它们是:企业经济责任、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法律责任和企业道德责任(或企业伦理责任)。其中,企业经济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对应;企业道德责任则与企业法律责任相对应。换言之,企业责任可依不同的标准进行划分:以目标的不同,可区分为企业经济责任和企业社会责任,前者主要以企业或股东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后者侧重于追求利润最大化之外的公益为目标;以是否规定于法律中,可区分为企业法律责任和企业道德责任,前者存在于法律之中,体现的是一定社会所认可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后者未上升为法律规范,而是寓于一定社会的道德观念和道德传统之中,它反映的往往是较高标准的道德要求。至于企业道德责任和企业法律责任之于企业经济责任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笔者的基本认识是:将企业责任划分为企业经济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以及将企业责任划分为企业法律责任与企业道德责任,这是企业责任的两种分类方式,在此基础上,企业经济责任和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分别进一步划分为企业法律责任和企业道德责任;同样,企业法律责任和企业道德责任也可以分别进一步划分为企业经济责任和企业社会责任。⑤这种认识的主要考虑是:企业经济责任和企业社会责任并不因为它们是否体现于法律之中而丧失其作为经济责任或社会责任的本质属性;同理,企业法律责任和企业道德责任亦并不因为它们所涉及的内容是经济责任还是社会责任而使其作为法律责任或道德责任的本质属性发生动摇。在对各种企业责任的大致意涵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作了上述描述后,我们来对国外学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些界定作一具体考察和评析。显然,在上文提及的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诸界说中,最适宜于在这里接受检讨的,当数Brummer和Carroll的观点。在Brummer的界定中,企业经济责任、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法律责任和企业道德责任都作为企业责任下独立的概念,这种把握应当说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Brummer看来,企业责任作一次划分就能同时得出该四种具体责任形态,或者说,企业责任等于这四种责任形态的直接相加,这样的认识就有失偏颇了。此种把依照多个标准对属概念进行划分而得出的所有种概念糅合在一起并同时作为属概念的对象范围的作法,不仅存在逻辑上的不严密,使企业经济责任、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法律责任和企业道德责任相互之间的关系发生混乱,而且也有碍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义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在企业责任中的恰当位置的正确把握。就Carroll的界定而言,我们以为有以下几个不妥适之处:一是,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个与企业责任等同的对象范围极其宽泛的属概念,使其不适当地包含了各种形形色色的企业责任类型;二是,将本应视为企业道德责任之组成部分的企业的慈善责任与企业道德责任并列,忽略了二者在本质上的一致性;三是,缘于第一点,这一界定使得企业经济责任、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法律责任和企业道德责任之间本来的逻辑关系变得紊乱。至于这三方面不妥的更具体的分析,上文已多有涉及,此处不再赘述。(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揭示在上文就企业社会责任诸界定所作的展示中,除介绍了美国经济开发委员会、Brummer和Carroll等所持的观点,我们还曾提到,学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尚存有其他一些分歧点。按照学者们的看法,这些分歧点都是在以内涵式界定法认识企业社会责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xii]在正式提出本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之前,首先有必要考究,学者们是否已真正揭示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对这些分歧,我们又抱什么样的态度?以下的分析,拟分别针对每一分歧点展开。之一,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构成是否应以慈善的或者热心公益的动机为条件,我们持否定的态度。除认可Davis、Blomstrom、Starling和Sturdivant对此所作的合理说明外,我们还认为,企业实施一项客观上利于公益之行为,其动机若何,实难认定,故而“动机”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成就要件,不具操作性。尤其法律已日渐介入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已非纯然的道德责任,依法律的引导乃至强制,或者迫于法律的威慑力而为对社会负责之举,即很难说企业具有热心公益的动机。在企业社会责任界定问题上,这一认识所隐含的意义是:企业的动机,非揭示企业社会责任内涵时所要考虑的因素。之二,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中应否包含“自愿”的内涵,我们亦持否定的态度。因为,既然企业社会责任包括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那么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就不应是全然的自由行为;对于怠忽承担法律规定的社会责任的企业,法律亦不会无动于衷。另外,企业社会责任最初就是因应社会舆论和社会压力的作用而产生,当前,我们固然应当倡导企业社会责任的自愿履行,我们也可以发现诸多开明的企业家自觉地使企业采取社会责任行动,但对于一些于社会公益和社会福利有重要影响的企业社会责任,我们不能放弃必要的、强有力的保障机制,而单纯地寄希望于企业的自发行动。上述分析暗含的结论是:自愿抑或非自愿,同样都不是界定企业社会责任时所应纳入考量的因素。之三,就“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中是否应包含诸如“为经济上的牺牲”之类的内涵,我们同样采否定立场。因为,正如Bock、Davis和Blomstrom等学者所言,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的利润目标有矛盾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缘于此,在某些场合,企业实施社会责任行为,须承受经济上的损失,或放弃经济上最有利于企业和股东利益的行动,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亦可能为企业和股东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尤其是践行企业社会责任,还有助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营造企业与社会的和谐、互动关系,这于企业的长期经济利益是大有裨益的。另外,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不难发现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蒸蒸日上、而怠忽企业社会责任者被最终逐出市场的实例。这意味着,企业社会责任之实行,可能导致企业经济上尤其是短期经济利益的牺牲,但并不尽然。既然企业社会责任可以通过、亦可以不通过牺牲企业经济利益的方式而付诸实行,那么我们也无必要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中注入“为经济上的牺牲”之类的内涵。之四,在“企业社会责任”强调的是行为本身还是行为之结果的问题上,我们倾向于此概念强调的乃一类行为。具言之,我们视企业社会责任为企业的义务,或者说作为一种对企业行为上的要求来看待,企业实施社会责任行为的实际效果如何,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性质决定无关宏旨。惟此,才能消除因惧于达不到预期目的而放弃社会责任行动的现象,以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也才可以避免同一行为对某些企业(实施该行为并达到预期目的的企业)是社会责任行动,于另一些企业(实施该行为但未达预期目的的企业)则非社会责任的悖谬。至于一些学者以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缺乏保障为由,主张企业社会责任的构成以行为目标的“圆满完成”为要件,藉此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落实,我们以为这一认识未免牵强,因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落实与企业社会责任本身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企业社会责任的落实取决于相应机制的确立,而不应寄希望于改变企业社会责任的本来属性。因此,不应在“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中注入“圆满完成”之类的限定。由上观之,英美学者在使用内涵式界定法把握“企业社会责任”时,其所概括出的所谓内涵,或者根本不能反映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之中,或者毋需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中专门作出说明。在此意义上,我们以为,英美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诸种内涵式界定,并未抽象出“企业社会责任”的真正内涵。三、本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考察和评说国外学者观念中的企业社会责任,其最终目的不外乎在于通过对各种观点的比较与扬弃,确立一种更加妥适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基于上述分析的结论,本文在此采信早期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者在使用“企业社会责任”一语时所表达的基本意旨,来对企业社会责任作一简短的定义,并围绕此定义作些必要的说明。我们认为,所谓企业社会责任,乃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公益的义务。企业社会责任与他种责任形态相比,具有以下几方面的质的规定性:(一)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关系责任或积极责任。析言之,“责任”一词包含两方面的语义:一曰关系责任,一曰方式责任。前者为一方主体基于与他方主体的某种关系而负有的责任,这种责任实际上就是义务;后者为负有关系责任(即义务)的主体不履行其关系责任所应承担的否定性后果。[xiii]企业社会责任实为企业的义务,尽管违反此义务将产生某种道义上的甚至法律上的否定性后果,但依各国学者的理解,后者并未纳入企业社会责任这一范畴。可以说,“企业社会责任”中的“责任”系指“义务”,这在学界和实务界都是一个无可置辩的定论。此外,我国法学界还将义务视为积极责任;将不履行义务所产生的否定性后果看作消极责任。若以此种划分法来看待企业社会责任,则它显然又属一种积极责任。(二)企业社会责任以企业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为企业义务的相对方。按照各国的通常理解,此所谓企业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之构成部分,系指在股东以外,受企业决策与行为现实的和潜在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影响的一切人。具体包括企业的雇员,企业产品的消费者,企业的债权人,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资源和环境、社会保障和福利事业的受益者等方面的群体。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者看来,因企业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在企业中存在利害关系(Stakes),故企业对他们的利益负有维护和保障之责,此种责任即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也便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对方。至于企业的股东(Stockholders),亦是一种重要的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企业对他们也负有直接的责任,此即实现其利润最大化的责任。然因企业对股东所负有的实现利润最大化责任乃企业经济责任而不归入企业社会责任之列,故股东应是企业经济责任的相对方而非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对方。(三)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的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的统一体。法律义务是法定化的且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其履行现实和潜在保证的义务。这种义务在法律中不仅有具体的内容和履行上的要求,而且对于其怠于或拒不履行也有否定性的法律评价和相应的法律补救,因此它实际上是对义务人的“硬约束”,是维护基本社会秩序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道德的法律化。道德义务是未经法定化的、由义务人自愿履行且以国家强制力以外的其他手段作为其履行保障的义务。这种义务的内容存在于一定社会的道德意识之中,通过人们的言行和道德评价表现出来。由于这种义务不以国家强制力为其履行保障,而只能通过义务人的责任感以及教育、规劝、鼓励、舆论评判等非法律手段的促使来确保其承担,因而它实际上是对义务人的“软约束”,是在法律义务之外对人们提出的更高的道德要求。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企业对社会负有的一种义务,并非单纯的法律义务或道德义务,而是这两者的统一体。这主要体现在,首先,从总体上看,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综合性的义务,它包括了企业对社会的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或言之,企业对社会的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统一存在于企业社会责任项下,共同构成完整的企业社会责任。其次,一项具体的企业社会责任往往包括了企业的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两方面的内容。例如,环境保护是企业的一项具体的社会责任,企业按照环境保护法规定的标准预防和治理环境污染,此乃企业的法律义务;企业依照比环境保护法的要求更为严格的标准预防和治理环境污染,这是企业的道德义务。而这两者同时划归企业社会责任之中,在各国几无争议。这就意味着,企业的环境保护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统一于企业的环境保护责任之中,共同构成企业的环境保护责任这一具体的企业社会责任形式。 (四)企业社会责任是对传统的股东利润最大化原则的修正和补充。传统的企业和企业法以个人(股东)本位为出发点,认为最大限度地营利从而实现股东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最高甚至惟一目标。企业社会责任则以社会本位为着眼点,认为企业的目标应是二元的,除实现股东利润最大化外,还应尽可能地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者看来,于利润和社会利益两方面的企业目标,任一目标的最大化都将受到另一目标的制约,因此,利润目标和社会利益目标经常处于深沉的张力之中。二者在相互约束的条件下实现其各自的最大化,便在企业目标上达致一种均衡状态。显然,企业社会责任是对股东利润最大化这一传统原则的修正和补充,且这一修正与补充并不否认股东利润最大化原则,其主旨,在于以企业的二元目标代替传统的一元企业目标。至于企业的利润目标和社会利益目标的冲突及其平衡问题,则正是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之提出和建构的出发点和归宿。 注释(注:为方便资料传递,本网站把原文的脚注改编成了尾注,且连续编号,但内容未变。如果引用,,请以原纸质文本为准)①指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二位学者贝利(Adolf A.Berle )与多德(E.M.Dodd,)就“公司的经理人员是谁的受托人”所展开的大讨论。②在《商事公司的社会责任》中,美国经济开发委员会开宗明义,提出了本报告的宗旨:“本报告讨论当代美国社会中商事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同时在对本报告的说明中还指出:“本报告的主要关注点,是企业责任中的社会方面而非经济方面,尽管我们承认,企业造福于社会,主要是通过发挥其生产产品和服务、创造财富的基本功能,来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p.9.)由此,美国经济开发委员会区分企业经济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略见一斑。③美国经济开发委员会所列举的第一类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行为,即“经济增长与效率”,具体包括:(1)促进私有经济部门的生产力;(2)增进企业管理层的创新力与绩效;(3)促进竞争;(4)在寻求更有效的抑制通货膨胀和实现高就业率的措施上与政府合作;(5)支持旨在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财政和金融政策;(6)致力于越战后的经济重建工作。④区分企业责任中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这是Brummer等学者讨论企业责任的初衷之一,但他们的这一愿望似乎并未真正实现。仅就其对企业道德责任之界定而言,即未能给出此一责任区别于其他类型的企业责任的本质属性。因为很明显,他所谓企业道德责任之四个构成要件,也可以是其他类型的企业责任所具备的。以企业经济责任为例,企业对它的履行与否的后果,同样具有理解能力;经济责任的履行对人类福利也有重大影响;企业对经济责任的履行及其效果,仍可以进行控制;社会对经济责任的履行,也并非没有一定的标准要求。对企业法律责任和企业社会责任来说,情况亦然。另外,Brummer等学者还认为,当事人负有依刑法从消极的角度所提供的行为标准行动的责任,此种责任乃道德责任;当事人行为不端,以致于有了犯罪意图和犯罪行为,即应接受道德上的归责,对当事人科以刑罚即是这种道德归责的体现(See Brummer,pp.24-25)。这就存在一些疑问:当事人依法行动为何不是法律责任(义务)?对犯罪给予刑事制裁为何又不是法律归责?综上观之,Brummer等学者关于企业道德责任与企业的其他责任的区分,尚显混乱,故而不足采信。⑤企业责任的两种分类方式可以通过以下二图示分别说明。(由于图表不能传递,故请参阅纸质文本。)应予说明的是,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国外学者在探讨企业社会责任时所提到的几种企业责任形态。从完整意义上讲,依目的的不同,企业责任可划分为三种形态,此即企业经济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对国家(或政府)的责任。其中,企业经济责任主要以个人本位为基础,企业社会责任侧重以社会本位为基础,企业对国家(或政府)的责任则着重以国家本位为基础。参考文献:[i] R. Gunness, Social Responsibility:The Art of the Possible, Business and Society Review,1986, p.25.[ii] Rutherford. Smith,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Term We Can Do Without, Business and Society Review, 1988, p.31.[iii] [韩]李哲松.韩国公司法[M]. 吴日焕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54-56.[iv] P. F. Drucker, 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1955, 转引自[日]金泽良雄.当代经济法[M]. 刘瑞复译,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105.[v]M. Firedman,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eptember 13,1970.[vi] C. Stone, Where the Law Ends ,1975, p.71, quoted in Dr Saleem Sheikh,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Law and Practice, CAVEndish Publishing Limited,1996, P.15.[vii] D. Votaw, Genius Becomes Rare in the Corporate Dilemma: Traditional Values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D. Votaw (ed.) ,1975, p.11.[viii]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Business Corporations, by the Research and Policy 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1971,pp.36-40.[ix] James J. Brummer,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and Legitimacy, Greenwood Press , 1991, pp.19-30.[x] Archie B. Carroll , Stakeholder Thinking in Three Models of Management Morality : A Perspective with Strategic Implications , in The Corporation and Its Stakeholders :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 , Edited by Max B.E. Clarks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1998, 139-170.[xi] Brummer, supra note 9,at 25-30.[xii] Ibid. at 26.[xiii] 张文显.法理学[M].法律出版社,1997.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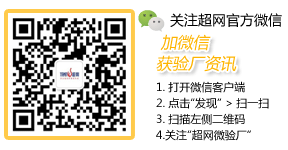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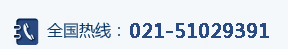
上海超网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 总部联系方式
- 电 话:021-51029391
- 电 话:400-680-0016
- 地 址: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银翔路655号
- 昆山分公司:18601606556---林经理
- 地 址:昆山市花桥国际商务区兆丰路18号亚太广场1号楼9楼
- 泉州分公司:0595-28069596---周经理
- 地 址:福建省泉州市温陵南路144号蟠龙大厦17D
- 宁波分公司:13615883698---周经理
- 山东分公司:18601606221---谢经理
- 温州办事处:18605772928----周经理
- 广东办事处:18601606206----周经理
- 企业邮箱:chaowang@tranwin.org




















